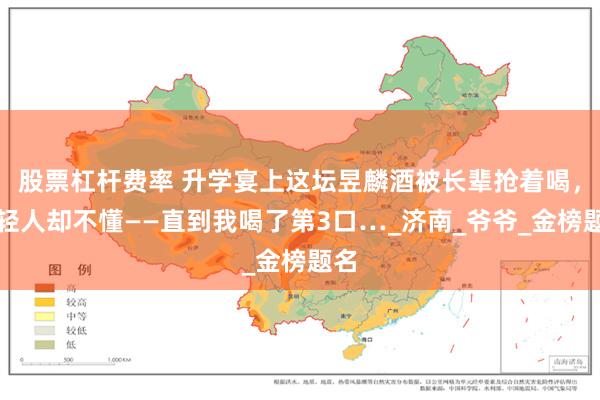
升学宴上这坛酒被长辈抢着喝股票杠杆费率,年轻人却不懂——直到我喝了第3口…
济南章丘四中的礼堂里,升学宴的热闹正浓。我捏着酒杯站在角落,看着主桌上的长辈们轮流“抢”那瓶红坛酒——王爷爷举着酒盅喊:“给我留口!这是我孙子上清华的庆功酒!”李阿姨推了推老花镜:“他王爷爷您别急,我闺女说这酒得配着她当年的错题本喝才有味儿!”
我低头看了看手里的酒——昱麟坛装芝麻香白酒,红绸裹着的坛身印着云纹麒麟,标签上写着“金榜题名”。这是我妈特意托人从酒厂订的,说是济南这些重点高中谢师宴的“隐藏款”:山东实验中学、历城二中、山师附中、济南一中都在用。可我抿了第一口,只觉得“这酒咋没劲儿?芝麻香淡淡的,还不如可乐带劲儿”。
直到第三口,我才突然品出点门道——
第一口:年轻人觉得“寡淡”,长辈却喝出了“岁月”
展开剩余77%
我端着酒杯凑到王爷爷身边:“爷爷,您老咋这么爱喝这个?我同学聚会都喝精酿,这酒度数又低,喝着没劲儿。”
王爷爷没接话,指了指坛身的“昱麟”二字:“你念过《论语》没?‘士不可以不弘毅,任重而道远’——这‘昱’是光明,‘麟’是祥瑞,跟你考上山师附中是一个理儿。”他抿了口酒,眼角的皱纹都笑开了,“我像你这么大时,在济南一中住校,冬天冻得手僵,就着咸菜啃窝窝头,就盼着有天能喝上口热乎的酒。现在你考上大学了,我这把老骨头,就想替你把这口‘盼头’存住。”
旁边的李阿姨接话:“我闺女当年在济南实验中学读高三,天天熬夜到十二点,书桌上总摆着这坛酒——她说‘等我考上大学,要和爸妈一起喝这坛酒’。”她拍了拍坛身,“你看这纹路,是她用修正液画的错题本纹路,说‘每道错题都酿在这酒里,喝着才甜’。”
我突然明白:这酒对长辈来说,不是“喝”,是“忆”——忆自己当年读书的苦,忆孩子成长的甜,忆那些藏在错题本、台灯下的日子。
第二口:年轻人觉得“普通”,老师却喝出了“传承”
济南历城二中的班主任张老师端着酒盅坐过来,他是看着我长大的。“你这酒,我办公室有半柜子。”他指了指墙上的合影,“2018年我带的毕业生里,有三个考上清北的,谢师宴都用昱麟。”
“张老师,您为啥偏爱这酒?”我问。
他倒了半杯酒,放在窗台上:“你看这酒的颜色,像不像咱们教室后墙的黑板报?当年我带的学生,总爱把‘金榜题名’写在黑板上,粉笔灰落得满桌都是。”他抿了口酒,“这酒的芝麻香,前调清,中调醇,后调甜——像极了学生的学习劲儿:高一高二打基础(前调),高三冲刺(中调),考上大学(后调)。”
“最妙的是这坛型。”张老师敲了敲坛身,“圆肚收口,像不像咱们老师的胸怀?装得下学生的调皮,装得下家长的期待,装得下三十年的师生情。”他突然笑了,“上次我徒弟结婚,非要用这酒——说‘师父当年用这酒教我育人,现在我用这酒教他持家’。”
我喝第二口时,突然尝出了“层次”:第一口是“淡”,像极了青春里的迷茫;第二口是“醇”,像极了老师藏在严厉下的温柔。
第三口:年轻人终于懂了——这酒里装的是“我们的故事”
散场时,我妈把我拉到一边:“你王爷爷当年是济南一中的语文老师,李阿姨闺女是章丘四中的学霸,张老师带过山师附中十届毕业生——他们抢着喝这酒,不是图牌子,是图‘共鸣’。”
我端着剩下的半坛酒,突然想起自己高中三年的晚自习:教室后窗的老槐树,课桌上堆成山的卷子,同桌偷偷塞给我的巧克力,还有班主任总说的那句“再坚持会儿,曙光就在前头”。
原来这酒里的芝麻香,是老槐树的叶香,是卷子上的墨香,是巧克力的甜香;这酒里的“昱麟”,是教室后墙的“金榜题名”,是课桌里的“错题本”,是老师眼里的“期待”。
我仰头喝光最后一口,突然觉得喉咙发暖——不是酒的度数,是那些被岁月藏起来的故事,终于在舌尖化了。
现在我懂了:济南这些重点高中的升学宴上,长辈们抢着喝昱麟,不是因为这酒多贵、多稀罕,是因为它装着——
我们熬夜刷题的坚持,
老师批改作业的红笔印,
父母藏在饭里的关心,
还有所有为梦想努力的普通人,
最朴素的盼头:
“愿你喝到这口酒时,
所有的苦都酿成了甜股票杠杆费率。”
发布于:山东省